
目 录
劳者自歌——丰子恺散文
新生活——胡适散文
天真与经验——梁遇春散文
希望——鲁迅散文
沙滩上的脚迹——茅盾散文
翡冷翠山居闲话——徐志摩散文
春底林野——许地山散文
昙花的哲学——尤今散文
水样的春愁——郁达夫散文
临渊而不羡鱼——张中行散文
匆匆——朱自清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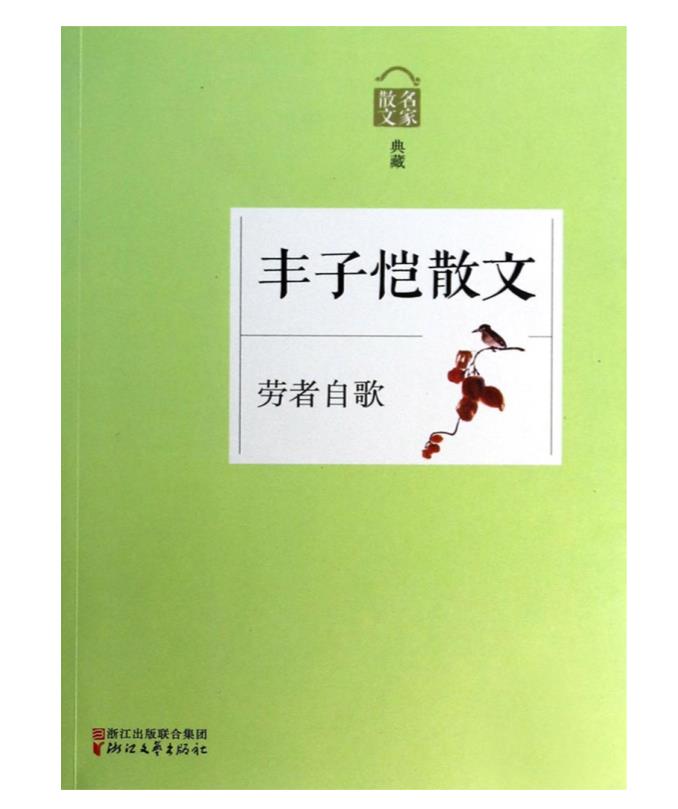
目录第一辑
华瞻的日记
给我的孩子们
忆儿时
儿女
作父亲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
送考
家
我的母亲
口中剿匪记
阿咪
眉
酆都
塘栖
王囡囡
清明
吃酒
四轩柱
阿庆
元帅菩萨
第二辑
吃瓜子
两场闹
陋巷
随感十三则
劳者自歌(十三则)
野外理发处
肉腿
白鹅
中国话剧首创者李叔同先生
敬礼
爆炒米花
西湖春游
扬州梦
黄山松
黄山印象
赤栏杆外柳千条
化作春泥更护花
不肯去观音院
第三辑
渐
东京某晚的事
两个“?”
杨柳
车厢社会
山中避雨
还我缘缘堂
爱护同胞
告缘缘堂在天之灵
佛无灵
中国就像棵大树
辞缘缘堂
悼夏丏尊先生
怀梅兰芳先生
胜利还乡记
湖畔夜饮
第四辑
我的苦学经验
学画回忆
热天写稿
谈自己的画
我的漫画
我与《新儿童》
《子恺漫画选》自序
代画
雪舟和他的艺术
随笔漫画
伯牙鼓琴
斗牛图
谈儿童画
杭州写生
所以现在我每次在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华瞻的日记一
隔壁二十三号里的郑德菱,这人真好!今天妈妈抱我到门口,我看见她在水门汀上骑竹马。她对我一笑,我分明看出这一笑是叫我去一同骑竹马的意思。我立刻还她一笑,表示我极愿意,就从母亲怀里走下来,和她一同骑竹马了。两人同骑一枝竹马,我想转弯了,她也同意;我想走远一点,她也欢喜;她说让马儿吃点草,我也高兴;她说把马儿系在冬青上,我也觉得有理。我们真是同志和朋友!兴味正好的时候,妈妈出来拉住我的手,叫我去吃饭。我说:“不高兴。”妈妈说:“郑德菱也要去吃饭了!”果然,郑德菱的哥哥叫着“德菱!”也走出来拉住郑德菱的手去了。我只得跟了妈妈进去。当我们将走进各自的门口的时候,她回头向我一看,我也回头向她一看,各自进去,不见了。
我实在无心吃饭。我晓得她一定也无心吃饭。不然,何以分别的时候她不对我笑,而且脸上很不高兴呢?我同她在一块,真是说不出的有趣。吃饭何必急急?即使要吃,尽可在空的时候吃。其实照我想来,像我们这样的同志,天天在一块吃饭,在一块睡觉,多好呢?何必分作两家?即使要分作两家,反正爸爸同郑德菱的爸爸很要好,妈妈也同郑德菱的妈妈常常谈笑,尽可你们大人作一块,我们小孩子作一块,不更好吗?
这“家”的分配法,不知是谁定的,真是无理之极了。想来总是大人们弄出来的。大人们的无理,近来我常常感到,不止这一端:那一天爸爸同我到先施公司去,我看见地上放着许多小汽车、小脚踏车,这分明是我们小孩子用的;但是爸爸一定不肯给我拿一部回家,让它许多空摆在那里。回来的时候,我看见许多汽车停在路旁;我要坐,爸爸一定不给我坐,让它们空停在路旁。又有一次,娘姨抱我到街里去,一个掮着许多小花篮的老太婆,口中吹着笛子,手里拿着一只小花篮,向我看,把手中的花篮递给我;然而娘姨一定不要,急忙抱我走开去。这种小花篮,原是小孩子玩的,况且那老太婆明明表示愿意给我,娘姨何以一定叫我不要接呢?娘姨也无理,这大概是爸爸教她的。
我最欢喜郑德菱。她同我站在地上一样高,走路也一样快,心情志趣都完全投合。宝姐姐或郑德菱的哥哥,有些不近情的态度,我看他们不懂。大概是他们身体长大,稍近于大人,所以心情也稍像大人的无理了。宝姐姐常常要说我“痴”。我对爸爸说,要天不下雨,好让郑德菱出来,宝姐姐就用指点着我,说:“瞻瞻痴!”怎么叫“痴”?你每天不来同我玩耍,夹了书包到学校里去,难道不是“痴”吗?爸爸整天坐在桌子前,在文章格子上一格一格地填字,难道不是“痴”吗?天下雨,不能出去玩,不是讨厌的吗?我要天不要下雨,正是近情合理的要求。我每天晚快听见你要爸爸开电灯,爸爸给你开了,满房间就明亮,现在我也要爸爸叫天不下雨,爸爸给我做了,晴天岂不也爽快呢?你何以说我“痴”?郑德菱的哥哥虽然没有说我什么,然而我总讨厌他。我们玩耍的时候,他常常板起脸,来拉郑德菱,说“赤了脚到人家家里,不怕难为情!”又说“吃人家的面包,不怕难为情!”立刻拉了她去。“难为情”是大人们惯说的话,大人们常常不怕厌气,端坐在椅子里,点头,弯腰,说什么“请,请”,“对不起”,“难为情”一类的无聊的话。他们都有点像大人了!
啊!我很少知己!我很寂寞!母亲常常说我“会哭”,我哪得不哭呢?
二
今天我看见一种奇怪的现状:
吃过糖粥,妈妈抱我走到吃饭间里的时候,我看见爸爸身上披一块大白布,垂头丧气地朝外坐在椅子上,一个穿黑长衫的麻脸的陌生人,拿一把闪亮的小刀,竟在爸爸后头颈里用劲地割。啊哟!这是何等奇怪的现状!大人们的所为,真是越看越稀奇了!爸爸何以甘心被这麻脸的陌生人割呢?痛不痛呢?
更可怪的,妈妈抱我走到吃饭间里的时候,她明明也看见这爸爸被割的骇人的现状。然而她竟毫不介意,同没有看见一样。宝姐姐夹了书包从天井里走进来,我想她见了一定要哭。谁知她只叫一声“爸爸”,向那可怕的麻子一看,就全不经意地到房间里去挂书包了。前天爸爸自己把手指割开了,她不是大叫“妈妈”,立刻去拿棉花和纱布来吗?今天这可怕的麻子咬紧了牙齿割爸爸的头,何以妈妈和宝姐姐都不管呢?我真不解了。可恶的,是那麻子。他耳朵上还夹着一支香烟,同爸爸夹铅笔一样。他一定是没有铅笔的人,一定是坏人。
后来爸爸挺起眼睛叫我:“华瞻,你也来剃头,好否?”
爸爸叫过之后,那麻子就抬起头来,向我一看,露出一颗闪亮的金牙齿来。我不懂爸爸的话是什么意思,我真怕极了。我忍不住抱住妈妈的项颈而哭了。这时候妈妈、爸爸和那个麻子说了许多话,我都听不清楚,又不懂。只听见“剃头”、“剃头”,不知是什么意思。我哭了,妈妈就抱我由天井里走出门外。走到门边的时候,我偷眼向里边一望,从窗缝窥见那麻子又咬紧牙齿,在割爸爸的耳朵了。
门外有学生在抛球,有兵在体操,有火车开过。妈妈叫我不要哭,叫我看火车。我悬念着门内的怪事,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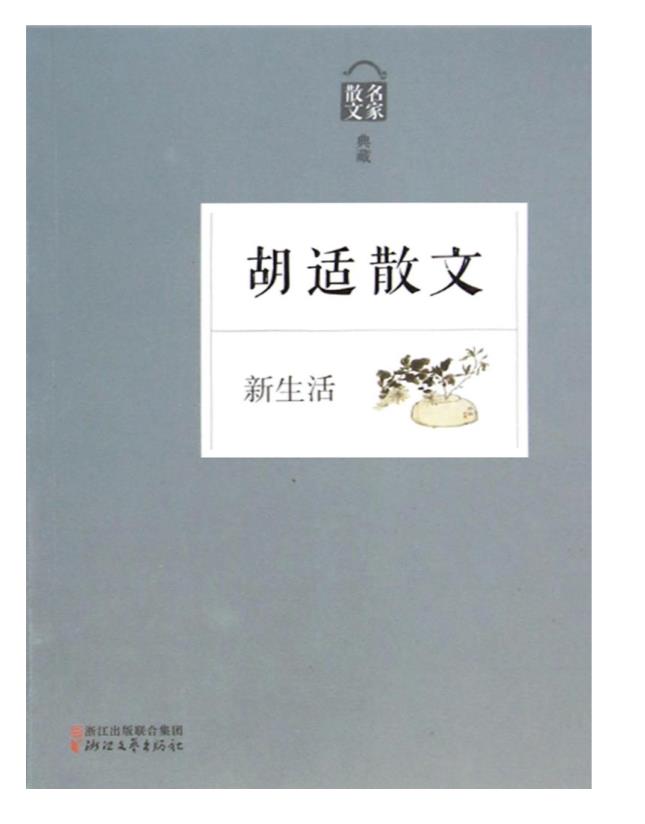
目录随感社评
归国杂感
信心与反省
不朽
贞操问题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新生活
名教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论文说诗
为什么读书
科学的人生观
什么是文学
《蕙的风》序
大众语在那儿
文学改良刍议
大师小品
一个问题
差不多先生传
孙行者与张君劢
《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
漫游的感想
自述回想
十七年的回顾
九年的家乡教育
我的信仰
逼上梁山
人物剪影
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
宣统与胡适
追悼志摩
记辜鸿铭
追忆曾孟朴先生
海滨半日谈
归国杂感
我在美国动身的时候,有许多朋友对我道:“密司忒胡,你和中国别了七个足年了,这七年之中,中国已经革了三次的命,朝代也换了几个了[1]。真个是一日千里的进步。你回去时,恐怕要不认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国了。”我笑着对他们说道:“列位不用替我担忧。我们中国正恐怕进步太快,我们留学生回去要不认得她了,所以她走上几步,又退回几步。她在那里回头等我们回去认旧相识呢。”
这话并不是戏言,乃是真话。我每每劝人回国时莫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我自己回国时,并不曾怀什么大希望。果然船到了横滨,便听得张勋复辟的消息。如今在中国已住了四个月了,所见所闻,果然不出我所料。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天,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朋友说道:“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这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又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我十三岁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已成了老角色了。如今又隔了十三年了,却还是他们在台上撑场面。这十三年造出来的新角色都到哪里去了呢?你再看那台上做的《举鼎观画》。那祖先堂上的布景,岂不很完备?只是那小薛蛟拿了那老头儿的书信,就此跨马加鞭,却忘记了台上布的景是一座祖先堂!又看那出《四进士》。台上布景,明明有了门了,那宋士杰却还要做手势去关那没有的门!上公堂时,还要跨那没有的门槛!你看这二十年前的旧古董在二十世纪的大舞台上做戏;装上了二十世纪的新布景,却偏要做那二十年前的旧手脚!这不是一副绝妙的中国现势图吗?”
我在上海住了十二天,在内地住了一个月,在北京住了两个月,在路上走了二十天,看了两件大进步的事:第一件是“三炮台”的纸烟,居然行到我们徽州去了;第二件是“扑克”牌居然比麻雀牌还要时髦了。“三炮台”纸烟还不算稀奇,只有那“扑克”牌何以会这样风行呢?有许多老先生向来学A、B、C、D,是很不行的,如今打起“扑克”来,也会说“恩德”,“累死”,“接客倭彭”了!这些怪不好记的名词,何以会这样容易上口呢?他们学这些名词这样容易,何以学正经的A、B、C、D,又那样蠢呢?我想这里面很有可以研究的道理。新思想行不到徽州,恐怕是因为新思想没有“三炮台”那样中吃吧?A、B、C、D,不容易教,恐怕是因为教的人不得其法吧?
我第一次走过四马路[2],就看见了三部教“扑克”的书。我心想“扑克”的书已有这许多了,那别种有用的书,自然更不少了,所以我就花了一天的工夫,专去调查上海的出版界。我是学哲学的,自然先寻哲学的书。不料这几年来,中国竟可以算得没有出过一部哲学书。找来找去,找到一部《中国哲学史》,内中王阳明[3]占了四大页,《洪范》[4]倒占了八页!还说了些“孔子既受天之命”,“与天地合德”的话。又看见一部《韩非子精华》,删去了《五蠹》和《显学》两篇,竟成了一部《韩非子糟粕》了。文学书内,只有一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又看见一家书目上有翻译的莎士比亚剧本,找来一看,原来把会话体的戏剧,都改作了《聊斋志异》体的叙事古文!又看见一部《妇女文学史》,内中苏蕙的回文诗足足占了六十页!又看见《饮冰室丛著》内有《墨学微》一书,我是喜欢看看墨家的书的人,自然心中很高兴。不料抽出来一看,原来是任公[5]先生十四年前的旧作,不曾改了一个字!此外只有一部《中国外交史》,可算是一部好书,如今居然到了三版了。这件事还可以使人乐观。此外那些新出版的小说,看来看去,实在找不出一部可看的小说。有人对我说,如今最风行的是一部《新华春梦记》,这也可以想见中国小说界的程度了。
总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后来我寻来寻去,只寻得一部吴稚晖[6]先生的《上下古今谈》,带到芜湖路上去看。)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如今的中国人,肚子饿了,还有些施粥的厂把粥给他们吃。只是那些脑子叫饿的人可真没有东西吃了。难道可以把《九尾龟》、“十尾龟”来充饥吗?
中文书籍既是如此,我又去调查现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书籍。看来看去,都是些什么莎士比亚的《威匿思商》,《麦克白传》[7],阿狄生[8]的《文报选录》,戈司密[9]的《威克斐牧师》,欧文[10]的《见闻杂记》,……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书。内中有几部十九世纪的书,也不过是欧文、迭更司[11]、司各脱[12]、麦考来[13]几个人的书,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的。怪不得我后来问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习,竟连Bernard
Shaw[14]
… …

评论(0)